【编者按】《消失中的食物》( [英]丹·萨拉迪诺著,高语冰译,文汇出版社·贝页2023年12月版)不仅是一部探讨全球食物多样性危机的著作,更是对地方种质保护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呼唤。在7月2日,由食通社与贝页图书联合发起的《消失中的食物》线上读书会中,围绕食物多样性与地方品种的保护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。两位嘉宾——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生邹磊和长期从事农村发展的廖凤连——通过自身的研究与生活经历展示了地方鸡种和赣南脐橙在现代农业、市场化进程中的困境与挑战。他们详细阐述了单一化养殖/种植、病害蔓延及产业化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深远影响,希望能够唤起更多人共同参与食物多样性的守护行动,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富而健康的饮食文化遗产。澎湃新闻经食通社授权刊发分享内容,经讲者审定。本文是廖凤连(风车)分享的“记忆中的水果:赣南脐橙产地的故事”。

本地李子,个头小
比如我们那边有本地的桃子,本地的李子品种也很多。现在我们那里的本地李子有许多也已经消失了。有些是红肉的,有些是黄肉的,有的个头小,有的个头大。但整体看,个头都比较小,不像现在买的三华李、蜂糖李那样大。

酸味明显的桃子
还有各种桃子,比如毛桃、酸毛桃,这两种桃子的个头都比较小,表皮有很多毛,味道也比较酸。另外,还有一种专门叫酸桃,果肉是深红色的,味道非常酸。还有各种水蜜桃,但是水蜜桃也不像现在市场上买到的那种水蜜桃那么大。
柑橘类的话,有各种橘子、柚子、金橘。还有一种我不知道它具体名称,只是我们那里叫“切柑”。为什么叫切柑?主要是因为它很难剥皮,需要切开来吃,而且特别酸。这段时间已经没有人在种了,所以大概就只有这些品种。
大多数水果都是自家吃,大部分都是野生品种,9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经过改良。这里又回到《消失中的食物》第57页提到的内容:为什么水果会越来越甜。实际上,我们不仅失去了对酸味和苦味的欣赏,还刻意把这两种味道从我们的食谱中去除了。现在市场上卖的水果大多以甜味为主。酸味的水果,消费者好像没那么喜欢。所以在植物栽培上,大家就更倾向于产出更大、更甜的橙子,然后运往世界各地。
现在我家是种赣南脐橙的。在脐橙成熟初期,味道会偏酸,经常会有消费者说:“为什么你们家的橙子这么酸?真的是正宗的赣南脐橙吗?”所以消费者也在选择,更喜欢吃甜的。书中也提到,这种趋势导致全球作物更容易受到虫害和疾病侵袭。因为人类选择了越来越甜的品种,也让害虫更容易繁殖,病虫害会更加严重。
野生柑橘中带苦味的化学物质,是植物天然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也能够让我回想起小时候的某些记忆,比如那种口感非常酸、很难剥皮的“切柑”品种,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由于水果越来越甜,就需要用更多的化学喷雾剂来保护果实。

成熟期的蜜橘

未成熟的椪柑
这些照片少数是我自己拍的,有些是网上找到的。还有一种类似山上的野生梨,非常小个,有些会长成大一点的梨,树很高,就是我们那边的老品种,叫张梨。我也不确定现在市场上还能不能买到,我们那边现在也很少见了。它的树高达三四米甚至四五米,特别难摘,但果实比野生梨稍大一些。
金桔在我们那边以前一直有种,现在则越来越少见。还有桔子,桔子分为早熟、中熟和晚熟三类。李子这边只有一种红肉、个头较小的,叫做五月李。这些都是我们家以前那边常见的一些品种。五月李是我家现在还在种的水果之一。以前我们家种的水果品种非常多,现在则少了一些。
90年代到2000年,果蔬品种整体是增多的趋势,本地和外地的品种都有,而一些本地老品种也依然保留在种植。同时,农户也会购买或嫁接外地商品性更好、糖度更高的优良品种,因此这些优质水果在当地市场上也能买到。
从90年代开始,我们当地有人开始专业从事果树种植,有专门的人育苗,他们不仅自己家种,还专门去周边各地寻找更好的品种,剪取枝条用于育苗和嫁接,然后再将苗木售卖给周边村民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果树。那时,村民会开垦荒山来种植果树,果农数量逐年增加。
那时候的品种还是比较多样化的,单一品种种植面积不会很大,每一种最多一两亩,大多数都是零散种植。水果采摘后,主要是季节性在本地销售,很少运到很远的地方。像我家,每年六月左右有水蜜桃,七月份有西瓜,八到十月有不同成熟期的柑橘类可以出售。我们那边的果农通常是将自家水果直接运到附近的墟市零售,90年代很少有批发,主要还是在当地市场销售。也因为主要在当地市场销售,所以种植面积不可能很大。
进入到2000年后,脐橙的规模化种植就开始了。过去只面向当地的小市场,但逐渐拓展到了全国的大市场。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发生了变化,从原来依靠多种不同季节的水果,转变为主要依靠单一的脐橙收入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比如说以前已经种过水蜜桃、李子、梨以及其他柑橘类水果的,都会把原有的沙梨、奈梨、桃子等果树砍掉,改种脐橙。同时,也会开垦更多的荒山建设果园,果树品种变得更少,但种植面积越来越大。具体种什么、种多大面积,都是由市场来决定。
大概是在2000年以后,在我们家乡这种变化非常明显。尤其是在2010年前后,我们那边无论是苗木培育、农资供应、仓储、销售还是物流加工等,全产业链都在本地形成了,区内有不同的公司或能人参与,分工已经非常明确。
本地的原生品种越来越少了。村民大多反映这些品种既不好吃,也不好卖。我前两天问了我妈,她也说,过去的这些品种不好吃,没有用(经济价值)。
以我自己家为例,原本就有本地的金桔、柚子、切柑之类的水果,但很少拿去卖。后来在九十年代,我们家开始积极地种植各种果苗,这样做,既是为了日常能够多吃些水果,也希望有些水果可以拿出去卖。只要能买到果苗或者能嫁接的,我们家都会尝试去种。这些果蔬既是自家食用,也在当地市场上销售。
也正是在这个阶段,比如说在2000年左右,我家一直都保留着早熟和中熟的蜜橘。这些橘子其实都是在九月份以前成熟,这样一来,它们就可以在九月份之前成为秋季学期学费的来源。
我也是前两年才知道,为什么我家一直保留这些橘子,而不是全部嫁接成脐橙。因为脐橙在十一月成熟,而橘子八九月份就成熟,这个时候可以销售一次,就会有一些现金流入。在2000年初以后,零几年那段时间,对我家的家庭收入还是很重要的。
等到产业化后,我家的晚熟橘子、沙田柚都嫁接成了脐橙树,过去的其他果树品种也砍掉种上了脐橙。所以我们那边柑橘类的品种就越来越单一,种苗的来源也变得越来越单一。
以往这些种苗可能会直接去集市,或者向亲戚朋友要。后来随着产业化发展,这些种苗都是要去专业的苗圃购买。尤其是黄龙病出现后,就更觉得要在专业苗圃购买脱毒苗木。如果自己嫁接或者自行育苗,就有携带黄龙病病毒的风险。所以现在,特别是《赣南脐橙保护条例》出台以后,对于市场上买卖这些脐橙苗的监管力度就更大了。
现在赣南脐橙的种植面积有200万亩,产值和品牌价值都非常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赣南脐橙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,比如黄龙病的泛滥、种植成本的飙升、农资成本和大棚等成本行情的不确定性。现在赣南脐橙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。

满山的防虫网,来自网络

部分搭建防虫网,来自网络
我们的许多果园其实是种在丘陵地带。携带黄龙病病毒的木虱,是一种非常小的昆虫,它会导致脐橙和其他柑橘类感染黄龙病。果农们都非常痛恨这种木虱,想要将其彻底清除,但又很难完全消灭。所以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户因为果园都在山上,就会为每一片脐橙果园搭建防虫网。
赣州市寻乌县连片的脐橙果园,绝大部分都已经搭建了防虫网,因此远远看过去,整座山都是白色的,每个山头都覆盖着防虫网。这种防虫网的成本非常高,大约每亩地需要1万元左右。
这种防虫网的稳固性也不太好,遇到大风大雨时很容易损坏,尤其是2023年的冬天,雪下得很大,也会导致网子塌掉。这样一来成本高,又容易损坏。因此,很多村民也并不会选择大面积搭建防虫网种植,尽管黄龙病的危害很大。
过去,脐橙产业化让一代人能够在家乡发展。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,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以通过种植脐橙安稳生活,满足日常开销、子女教育、修建新房等支出,都是依靠种植和销售脐橙获得的收入。但现在,脐橙产业面临巨大的挑战。
针对黄龙病,目前的措施有“三板斧”:第一板斧是砍除病树,也就是发现脐橙感染黄龙病后要立刻砍掉。果业局会在冬季或春季统一组织砍树,农户也会自行砍除。第二板斧是杀灭木虱,主要是农户勤打药,尤其是在夏秋季节新叶萌发期,需要非常勤快地打药,可能每隔一周甚至十天就要打一次。此外,果业局这几年也会统一组织飞防作业。
第三板斧就是推广脱毒苗木的种植。这样一来,市场上就禁止销售自家的嫁接苗,农户必须去专业苗圃购买脱毒苗。还有一些其他的做法,比如农户自己主动搭建防虫网,但这个成本很高,并不是所有农户都会选择。还有一种方法是设置隔离带,比如在果园四周种植杉树,或者选择相对独立、周边没有其他果园的地块建立果园。
另外,如果你的果树已经四五年,进入了挂果期,但又感染了黄龙病,怎样延缓病情,让果实还能转绿呢?
有些村民选择为这些树“打吊瓶”,其实是注射抗生素,可以在树体内抑制黄龙病,但病毒依然存在树体上,只是能够延缓两三年树的死亡。
《消失中的食物》第59页提到了印度的野生柑橘林。现在全世界大约有10亿棵柑橘树,表面上看,失去野生柑橘林似乎不是问题,但实际上,这些野生柑橘林拥有对抗疾病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独特基因。
黄龙病这种细菌感染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摧毁柑橘产业,迫使一些果农停业、失业。这种情况也正在江西赣州等地发生。最近佛罗里达大学宣布了一个研究突破,他们在与古老的野生柑橘接近的品种中,找到可控制黄龙病的基因。保护这些野生果树的土著居民,实际上在守护能够拯救10亿棵果树的关键基因。我也很期待这个研究能够取得真正的突破。因为目前黄龙病被称为柑橘类的“癌症”,现在还没有攻克这一难题。当然,我们那边的村民也在说,如果真能攻克这个难题,赣南脐橙可能会变得很普遍,现在其实已经很普遍了,种起来会更难,价格也会更便宜,似乎也不一定是好事。
其实这不仅仅是单一产业化和单一作物种植的问题,不只是记忆中的味道消失了,比如我小时候从小吃到的那些水果已经消失了,这其实也是过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并逐渐消失的过程。
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,本文标题:《我们真的吃得越来越丰富了吗(二):记忆中的水果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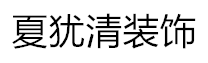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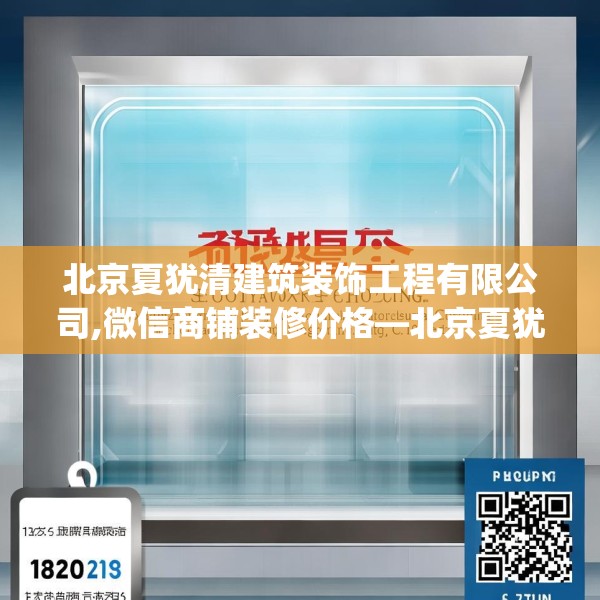



 京ICP备2025104030号-22
京ICP备2025104030号-22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